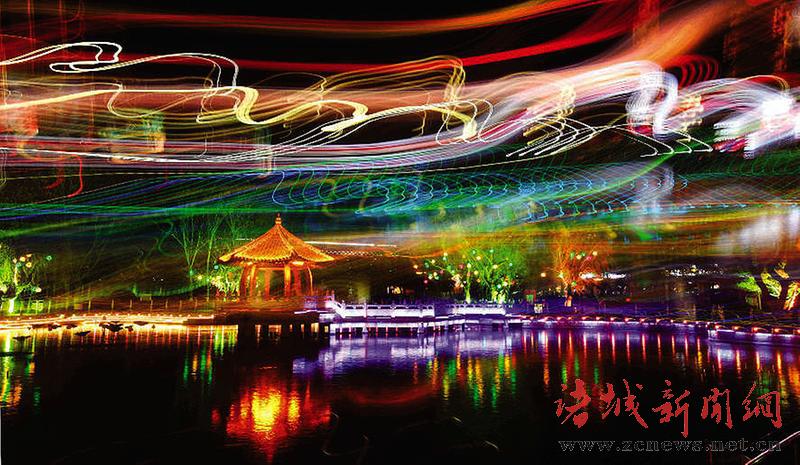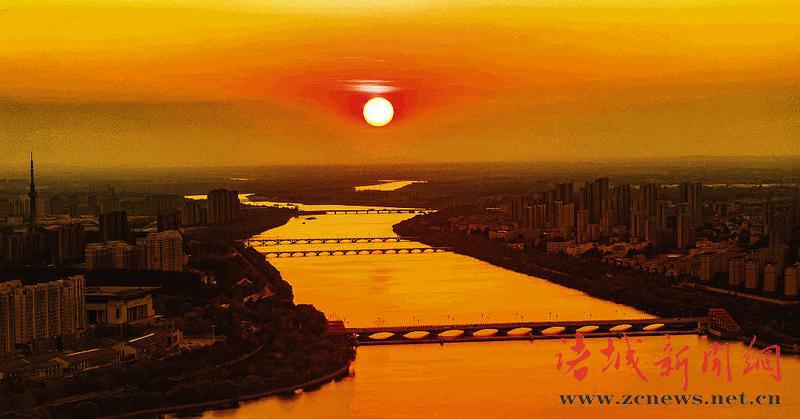父亲经常会俯身大地,努力耕耘。在风调雨顺的日子里,全家老少吃饱穿暖,身体健康、强壮是父亲的希望。
由小麦到馒头,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走进了我们的一日三餐,所以我特别珍惜今天的丰衣足食。无论离家多远,无论身在何处,只要到饭点,我仿佛都能闻到馒头的馨香。
从每年的秋收之后,十月一左右,小麦的种子就在泥土里发芽,成长。直到来年的芒种时节,端午前后的收割,小麦完成了历经严冬、春寒和夏烤的考验,最终颗粒归仓。
新收的小麦,要进行完一个隆重的仪式,我们才能享用。在我们这儿六月六之前要上新麦子坟,就是用新麦子馒头去祖坟上先祭拜、供祖。母亲会用一个大三盆倒上小麦,用水淘洗,再用干净的包袱把麦子外皮的水擦干,放在一张不用的大炕席或薄膜上晒干,到村里的磨坊磨成面粉。做馒头是母亲的拿手活,母亲用大八印锅蒸的馒头,松软适中,我百吃不厌。
天天吃上白面馒头,是祖辈和父辈们的梦想。在缺吃少穿的年代,父辈们吃了不少苦,遭了不少罪。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是他们梦想实现的见证。
记忆最深的是母亲过年做馒头,用老面做面引子,揉成一块一块的面团,发酵,再分成馒头大小,经过反复搓揉,做成馒头。
我能天天吃上馒头是在一九八五年上高中时,那时我们都在学校投粮寄宿,每月二十八斤粮。一天一斤粮对我们女生来说还行,男生往往饿得晚自习后找我们女生的课桌洞,希望能找到我们吃剩下的馒头。记得有一次晚自习后,几个男生没有找到馒头,发现了一个女生课桌洞里有一瓶益母草膏,还有滋有味地尝了尝。那时候,我们每星期五下午有两节劳动课,老师会把我们分成几组,有打扫卫生的;有去学校操场边的小菜园拔草的;有去食堂帮着蒸馒头的。我们都愿意去食堂帮工,食堂的老师有时会给我们点好吃的打打牙祭,帮完工还能给我们几瓣大蒜或几块咸菜。食堂里蒸馒头的蒸笼很大,一次放好几层,全用机器和面,做馒头,我们的任务是把从机器出来的长条形的馒头板板正正地放在圆形的大蒸笼里。每个馒头二两半,一天一斤馒头。我的安排是这样的:早上二两半,中午半斤,晚上二两半,中午吃不上剩点晚上吃。我们吃饭用饭票,值日生轮流负责全班同学的喝水吃饭。每班一个竹片编的盛馒头的大筐,一根扁担和两个水桶,两人一组打水,两人一组打饭。有一次轮到我和同桌去抬回馒头筐,分完了同学们的馒头,我的没有了,就坐在课桌旁哇哇大哭起来,把同学们吓了一大跳,生活委员李月亮赶紧拿了自己的馒头给我送了过来。
我蒸馒头是在参加工作成家之后,工作之余,我们闲聊,不知谁先扯到蒸馒头上,我们几个女人的笑声传出老远。邵大姐第一次蒸馒头没等面发蒸成了石头疙瘩,被她对象用包袱背回了娘家,还说是闺女孝敬老娘的;李大姐第一次蒸馒头面软了,从蒸笼的缝里挂起了面条;张大姐把馒头蒸糊了……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娘在灶台蒸馒头,我叫了声娘,娘像没听见没回应,我大声叫了一声,梦醒了,隐隐约约感到肚子有点饿。想娘了,想吃娘蒸的馒头了。
刘明芬 (作者系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诸城作协会员)
1 条记录 1/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