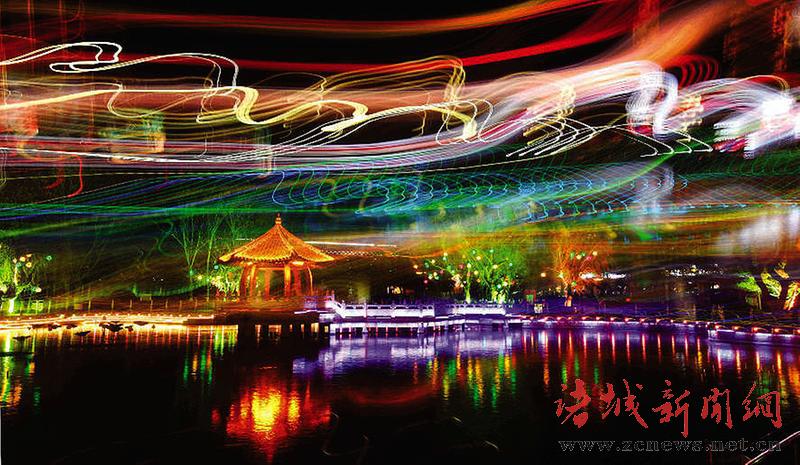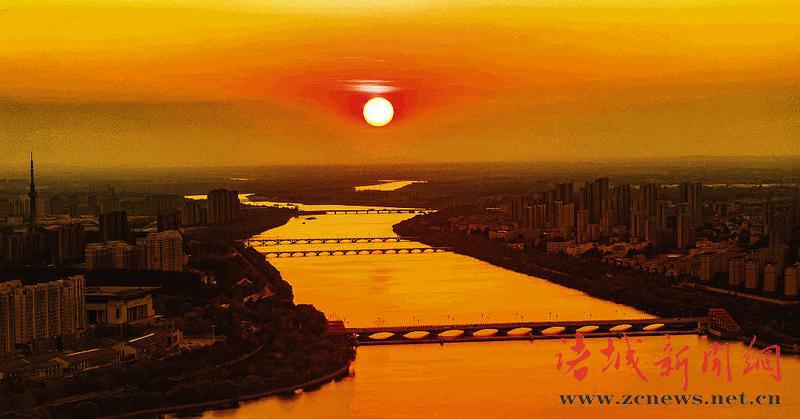小时候,每个节日对孩子们来说都很重要。小年,也是眼巴巴数着指头盼来的。是大年的前奏、序曲,是忙年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小年这天,最忙的活是扫屋。只要不是很糟的雨雪天气,屋是必扫的。早早地吃过饭,便往天井里搬弄东西。箱子柜子大桌子是大物沉物,父亲和母亲抬,盘碗盆子杌子暖壶等零七碎八的东西,我们几个孩子出出进进地往外倒腾。阳光好,正好晒席子、铺炕草、被子。炕东头的地瓜囤子用油纸或破衣服盖好,其它家什都收拾出来,散落在院子里。
父亲开始扫屋。大苕帚绑在一根长杆子上,父亲头戴破苇笠,脖子上围根破毛巾,仰着头,瞇着眼,抿紧嘴,哗哧哗哧,蛛网吊灰积尘纷纷落下,土墙上留下一线线纵横的痕迹。有了大扫帚后,父亲也挥着大扫帚扫够得着的地方。
父亲扫完出来的时候,满脸灰渍,尤其鼻翼两侧和下巴上,如墨画。我们都看着父亲笑,说成大花脸了,父亲也笑。过一会儿,父亲抱着草在堂屋里点上,父亲说用火把灰引下来。只见灰片如蝶乱飞。一半会儿也不能进屋,得等灰尘落净。
趁这空,父亲让我们拣拾石头砖头,他拿着锤子堵耗子窝,有的堵前先用水灌一会儿。母亲又吩咐我们洗刷饭桌子、菜板。只要父母不盯着,我们就去翻弄箱子柜子笸箩,连家里有几根缝衣针几个鞋钉子都一清二楚。那天家里人都将套了一冬棉衣的褂子脱下来,母亲泡了洗,差不多用去半条青松牌肥皂。印象中,母亲从井里现提水,说现提的水不冷。母亲绾着袄袖子,盆子里的水黑乎乎的。母亲的手通红通红的,纹理格外醒目。没有别的罩衣,我们都穿着空心袄,跑来跑去的也不觉得冷。
那天,多数得晒白菜。一人下到窖子里,一人等在窖口,霉味潮湿味土腥味一股脑冲出来。白菜被一棵一棵地递上来,撕去烂坏了的菜帮子,再提溜到向阳的墙根,让这些独脚菜一棵一棵倚着墙站好。照看白菜的差事也是我的。有时极不愿意,但也得看。嘟着嘴,走来走去,很无聊。家家有白菜,没人偷,也不怕鸡们来吃,撑死也吃不了几个叶子,要防的是那些野撒着的猪。让猪逮着空,要把猪八戒的大肚子填满,那可糟蹋白菜了。
到中午时得给白菜翻身,让全身都享受阳光的爱抚。吃饭也要倒班,那顿饭最潦草,热水泡碗煎饼,不用安饭桌,饭桌还在天井里晒着。就在锅台上,或坐在门槛上,三下两下扒拉进肚。也不用吃太撑,留着肚子晚上吃饺子。
看看太阳也懈了,就往屋里收拾东西,各就各位,旧物换新颜。眼里亮堂,心里也亮堂。白菜们带着阳光的味道,又被请进了窖子里。收拾下散落的叶子,扔到圈里,大耳朵猪吭哧吭哧美食了一顿。想溜出去玩,早被母亲瞅见了,吩咐扫天井。母亲洗完衣服,将各家什安妥好,就剁馅,和面,包饺子。年少不懂父母心,那天最忙最累的是母亲。
父亲找出灶屋爷爷画,剪下上边窄窄的一条,再把画端端正正地贴在靠近锅台的墙上。剪下的那片夹在一摞烧纸里。灶屋爷爷面前放张高凳子,摆上一盘软枣———用纸包着,藏着的,不知从哪里找出来的,怕我们偷吃。还有一个盘,放两块水果硬糖,或者两三个柿饼子。还有一个茶碗,盛上半碗黍子、秫黍或玉米,父亲说是马料,灶屋爷爷骑着马上天,好喂马。我们听得云里雾里的。父亲就耐心地说,灶屋爷爷是一家之主,家里的一切他老人家都看在眼里。每年腊月二十三,灶屋爷爷要上天,跟玉皇大帝汇报这一家人一年里的作为。所以,这天晚上,家家户户包饺子,放鞭炮,摆供品,烧纸,欢送灶屋爷爷上天。怪不得母亲太阳还老高就下手包饺子。我们不太关心灶屋爷爷上天说什么,更关心摆的糖果,在灶屋爷爷前转来转去。父亲说,是给灶屋爷爷吃的,谁也不敢动。那年月,除了过年,哪有糖果吃?也难怪孩子们馋得眼花花的。
母亲煮好了饺子,先捞上三碗———每碗也就四五个,父亲双手端着摆在灶屋爷爷面前。灶屋爷爷慈祥的眉眼氤氲在热气里。父亲烧纸,口中念念有词,后来知道就是“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之意,也知道摆上糖果之类甜食,是让灶屋爷爷吃得美美的,在玉帝面前多多美言几句———我仔细留心过,摆上的东西,一点都没动没少。父亲接着去天井里放鞭。村子里鞭声震天,响成一片。我们躲在堂屋门口,双手半捂半遮着耳朵,看浓厚的黑夜在耀眼的火花里四散溃逃。猜测着哪支鞭是小胖家放的,哪支是锁头家的。争吵声被扑鼻的饺子香打断。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桌,一阵囫囵吞饺,每个孩子都有了蜘蛛肚。父亲不急,倒一小壶酒,再倒满一小盅,放上一小片纸,点燃纸,酒也被烧着了,窜出红蓝的火焰,父亲将纸片拽出来,端起酒壶燎酒,酒味满屋子里窜。父亲说,水饺是最好的酒肴。
重铺好的炕,蓬松的炕草,干净的席子,散发着阳光的味道,又暄又热乎。我们忍不住在上面翻滚,折跟头。父母呵斥说,吃了一肚子饭,不能翻动,小心肠子。
那些年,父亲称小年叫“辞灶”,是灶屋爷爷临时离开家,去天上述职。灶屋爷爷,很多地方叫灶王。后来,看了些关于祭灶和灶王的传说,知道父亲的一些做法并非迷信,而是民俗,属于传统文化。
那时,对灶屋爷爷很敬畏,怕做了什么坏事落在他老人家眼里,到时跟玉皇大帝告一状,肯定没有好果子吃,便有了自律。也常常心怀侥幸,我跑到许多人家看过,所有人家的灶屋爷爷都是同一个人,千家万户的事都由他来掌管监督,忙得过来吗?
小年到了,大年还会远吗?近在咫尺的期盼给孩子们带来了无尽的快乐。
(作者系山东省作协会员)
1 条记录 1/1 页